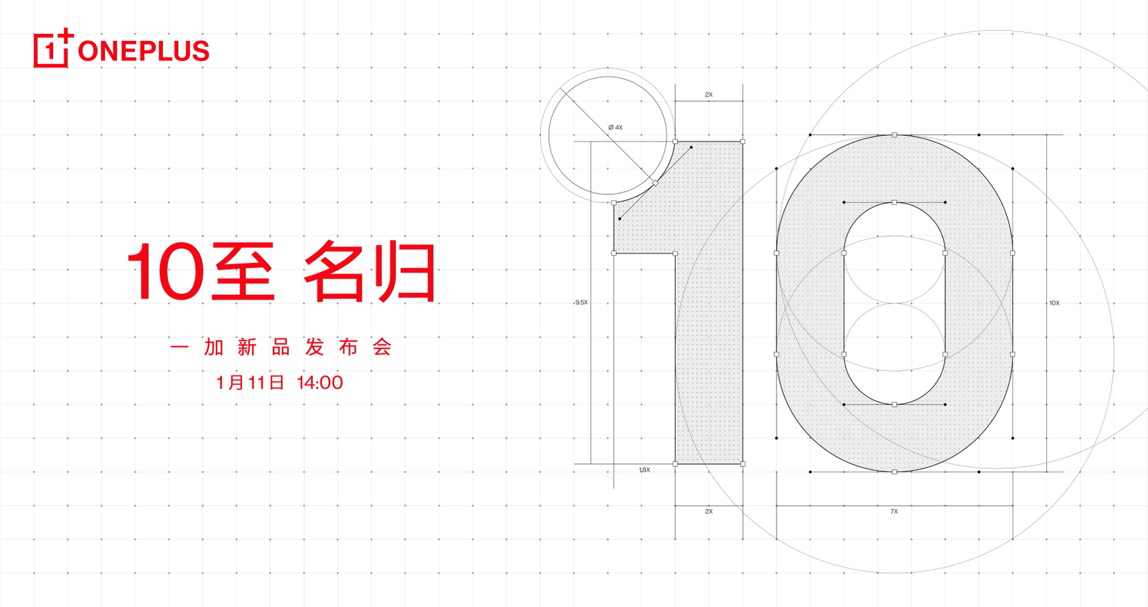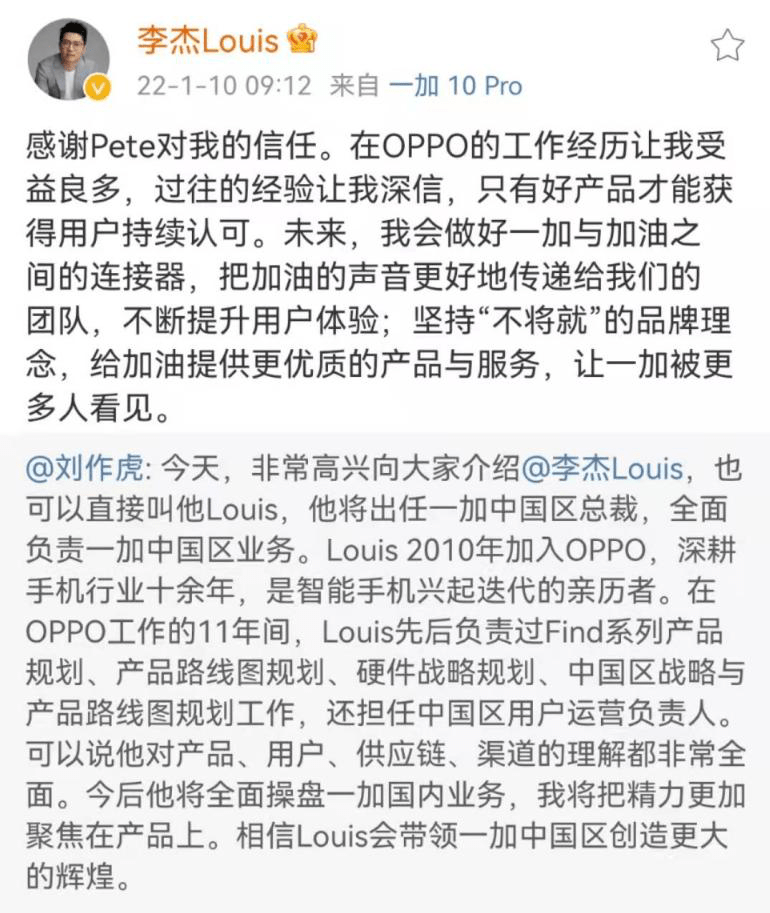隐藏的植物记忆:遗忘可能是更强大的生存工具
据国外媒体报道,在世界的另一个伟大王国中,正在悄然进行一场革命……
莫妮卡·加利亚诺(Monica Gagliano)开始研究植物行为,是因为她厌烦了做完实验就要杀死进行实验的动物。现在她是珀斯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位进化生态学家,当她还是一名博士后生的时候,就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在植物上,在实验室里有时不得不杀死实验动物,但如果将植物作为研究对象,只需取下一片叶子或者部分根茎就可以作为样本。当她将专业课题转移在植物研究上时,她仍将某些动物领域的观点带到了新研究课题之中。她很快开始思考植物是否具备类似动物的特征,或许植物存在行为方式、具有学习和记忆能力。
莫妮卡·加利亚诺(Monica Gagliano)开始研究植物行为,是因为她厌烦了做完实验就要杀死进行实验的动物。她认为植物也存在着记忆。
莫妮卡说:“开始一项研究,就像打开一个盒子,里面有许多的问题,你自然会依据线索和证据进行探索分析。有时你会发现自己像科学家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一样研究植物。”
在莫妮卡首次研究植物学习能力的实验中,她决定用研究动物的方法研究植物,她从最简单的学习形式入手——习惯性,如果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无害的刺激,它们的反应会发生变化吗?
含羞草具有几天的记忆能力
莫妮卡对含羞草(mechanical stimuli)进行了实验,它会对陌生的机械性刺激产生剧烈反应——叶片闭合,这可能是为了吓退那些急切的食草动物。在最新实验中,莫妮卡对含羞草设计了一种特殊的轨道,她将含羞草从轨道上方扔下,让它体验游乐园里的过山车,她发现含羞草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叶片紧闭。但是,当莫妮卡以60次扔下为一组,重复7组之后,植物的反应发生了变化,没有多久,含羞草在跌落轨道时就毫无反应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含羞草已经疲惫不堪,但莫妮卡用手摇动含羞草时,它们还会紧紧地闭合叶片,就好像它们知道从高空抛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3天之后,莫妮卡再次回到实验室,对同一批含羞草重复进行实验,当它们从轨道上方下降时,依旧毫无反应,这些植物和之前的反应一样。这个实验结果令大家十分吃惊,在对蜜蜂等动物为对象的实验中,持续24小时的记忆就是长期的了。莫妮卡没有想到,植物能够记住几天之前的实验训练,她说:“6天之后,我再次进行这项实验,原本认为含羞草会忘记轨道体验,但是它们仍还记得,就像是跟接受了训练一样。”
图中是含羞草,当人们接触其叶片时就会自然收缩起来。
她等了一个月,再次进行这项实验,结果显示含羞草的叶片保持张开,依据科学家对动物实验的惯例,他们推断含羞草已表现出一定的学习能力。在对植物王国的研究中,缓慢的革命正在悄然进行着。科学家开始意识到植物具有学习能力,之前没有注意和想像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只会将动物联系在一起,依照动物实验的观点,植物会看、听,并且知晓它们所处的世界。近期一项研究发现植物胚胎中的细胞簇就像大脑细胞一样,能够帮助胚胎决定何时开始生长。
在植物可能被忽视的才能中,记忆力是最有趣的一个,有些植物的生命只有一个季节,有些植物却能存活几百年时间,不管怎样,这些植物都能够记住过去的事情,以改变它们应对新挑战的方式。但是生物学家已经证明,某些植物在特定情况下,能够存储关于它们的经验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指导它们的成长、发展和行为。至少从功能上讲,它们似乎是在创造记忆内容。它们如何形成这些记忆,可能会帮助科学家训练植物面对各种挑战——贫瘠的土壤、干旱、极端高温等,这种频率和强度都在不断地增加,但是科学家必须首先明白:植物能记得什么?哪些记忆最容易忘记?
“植物认知”真的存在吗?
科学家一直回避研究所谓的“植物认知”,部分原因在于它和伪科学之间的关联,1973年颇受读者欢迎的《植物的秘密生命》一书就是这种伪科学的代表。某些类型的植物记忆也被混淆,这些都是关于进化论遭受置疑的理论。其中最容易理解的植物记忆形式就是春化现象(vernalization),植物对长时间的寒冷会留有印象,这能帮助它们确定开花的最佳时机。这些植物会在秋季生长得更高,冬季处于休养状态,到了白天时间较长的春季就会开花,但是前提是植物保留着过冬的记忆。这个富有诗意的观点与争议性最大的前苏联科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密切相关。
在职业生涯早期,李森科发现冷冻种子能将冬小麦变成春小麦,正常情况下,冬小麦是秋季播种,第二年春季收获;春小麦是春季播种,当年秋季收获。本质上讲,他在植物中植入一个错误的记忆,这些植物需要一个寒冷的信号才能生长。尽管李森科有这样的见解,但他仍然算不上是什么优秀的科学家。20世纪20年代末,他发表了关于春化现象的早期研究报告,前苏联政府随即开始搜寻一种农业灵丹妙药,金钱和名利充斥着这一领域。当李森科掌获权力时,针对自己当初的想法发表了一些令人愤慨的言论。他说:“春化现象可以改变所有各类的植物,其中包括:土豆和棉花,并且能大幅增加农作物产量。”
这些说法的证据并不充分,但这并不重要。1936年,李森科是前苏联政权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在政府指派哲学家的帮助下,李森科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个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与法国自然学家珍·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李森科认为,春化植物的后代可以继承后天习得的特性,因此通过改变环境,他可以培育比传统育种技术时间更短的农作物新品种。他的观点带来刻板的政治色彩。
美国哈佛大学退休历史学家罗兰·格拉哈姆(Loren Graham)研究分析了李森科的技术观点,他说:“李森科的理论都是基于一个原则进行的延伸,即基因并不是非常重要。李森科对于基因的存在了解甚少。”
事实上,李森科的理论被彻底推翻了,他无法培育出继承冬季记忆的新品种农作物。李森科曾承诺使前苏联的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但是1946-1947年出现的大饥荒中,他的理论并未拯救这个国家。当遗传学家开始置疑李森科的理论时,李森科对他们进行了公开抨击,这一事件导致数百位科学家监禁或者迫害死亡。李森科是导致俄罗斯一代遗传学家迫害致死的罪魁祸首,他们的选择是:要么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离开祖国;要么面对李森科的处罚。没有这些遗传学家,李森科永远不会明白自己在哪些方面是对的(植物能形成过冬记忆),在哪些方面是错的(至少这种类型的记忆无法遗传后代)。而在西方进行努力研究的一代科学家揭开了李森科自称的春化现象的真实秘密,虽然李森科声称春化现象的深入研究是自己的功劳,但从未真正地理解这一现象。
就在李森科提出其夸大主张时,铁幕的另一面科学家正在理解春化现象是如何运作的。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包括德国科学家格奥尔格·梅尔彻斯(Georg Melchers)和安东·朗(Anton Lang)在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梅尔彻斯是植物发育领域的资深生物学家,而安东是一位无国籍难民生物学家,他们在一起研究春化现象,寻找开花的生物化学秘密,结果显示其秘密在于一种叫做“成花素(florigen)”的植物激素。
艺术家描绘的莨菪植物,茛菪是两年期植物,其生命周期会持续两个生长季节。第一年春季和夏季,茛菪会尽可能生长,但抑制自己开花;第二年春季,茛菪才会开花,结出乳白色的花朵,花心的紫红色沿着叶片脉落遍布整个花瓣
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叫做茛菪(henbane)的茄科植物,一些植物到达其发育的特定时期会开花,就像青少年进入青春期开始炫耀其新出现的性特征一样,完全不顾后果。而有些植物就像暑假开始疯狂玩耍的青少年,只有接收到来自环境的信号才开花。茛菪又被称为“天仙子”,它属于后者情况,需要度过一段寒冷时期,在光照充分的情况下才会开花。与在一年时间内生长、死亡的一年期植物不同,茛菪是两年期植物,其生命周期会持续两个生长季节。第一年春季和夏季,茛菪会尽可能生长,但抑制自己开花;第二年春季,茛菪才会开花,结出乳白色的花朵,花心的紫红色沿着叶片脉落遍布整个花瓣。对于两年期植物而言,这种双重要求是有道理的,它能阻止植物在秋天开花,秋季光照情况虽然理想,但是寒冷的冬季会毁灭它们的花朵。
当科学家试图理解春化现象和白昼长度是如何协同运行使茛菪开花时,梅尔彻斯和安东探测到茛菪的冬季记忆极限。在一项实验中,他们将茛菪放在冰箱中进行冷藏,使其进行“春化”,之后再将这些植物放置在温暖的环境中,试图逆转其春化过程。冷藏一两天之后,科学家仍能对茛菪进行“逆向春化”。但是冷藏4天之后,春化已经无法逆转,事实上,这意味着每年2月份的一场温暖天气不会骗过茛菪,让它们忘记之前数个星期的持续寒冷。在另一项实验中,梅尔彻斯和安东控制白天光照时间,这种春化植物继续生长,但并未开花。即使10个月之后,他们为茛菪提供一整天的光照条件,告诉它们现在处于最佳时机,茛菪竟然还会开花,这些植物的过冬记忆持续了近1年时间。
梅尔彻斯和安东并未将春化现象描述为“植物记忆”,但是现今它是最值得研究的一个例子。这些实验表明,植物能保留过去的记忆,甚至记忆力也比人类想象中持久得多,像秘密特工一样,完全接受训练,随时等待信号进行行动。
当多数人在观看一株植物时,都很难想像它是在等待什么,植物似乎并没有长远计划,如果它们缺水,就会萎缩,如果雨水过多,它们就会振作起来,如果阳光充分照射,它们就会朝向太阳方向生长。从人类的思维角度思考,植物并没有做什么,但是仅是观察其他人和狗的行为,我们也意识不到人类和狗的记忆。当你喊他们的名字时,别人会对你微笑,狗会朝向你跑来。相比之下,对于含羞草和茛菪而言,过去的经历也会改变未来的反应,我们并未注意或者对于其原因无从知晓。
二十世纪80年代,科学家才开始首次探讨“植物记忆”,例如:当时一支法国研究小组碰巧发现,某种植物记得一侧叶片曾受过损伤,因此集中其能量朝向另一个方向生长。从那以后,科学家发现一些植物具有一定的记忆,它们会记得干旱、脱水、寒冷、炎热、强光照、酸性土壤、短波辐射,以及害虫啃食叶片等经历。当植物再次面对同样的生存压力,植物会调整自己的反应,它们可能会提高锁水量、变得对光更加敏感、增强耐盐和耐寒性。在某些情况下,植物的记忆会遗传给下一代,正如李森科所认为的那样,尽管植物记忆完全不同于他想像的方式。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植物的能力被大大低估了。它们能够“听到”震动,这可能有助于识别昆虫的袭击。它们还可以通过空气和根部传播化学物质,分享信息。在有关植物形成记忆的研究中,下一步将了解它们是如何实现的。
揭晓植物记忆必须了解表观遗传学
在梅尔彻斯和安东的时代,激素是植物科学的前沿科学,发现新激素的技术也非常简单暴力:科学家先将叶片磨碎,之后分离提取植物释放的小分子,然后他们把这些激素喷洒在植物上,观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例如:赤霉素(Gibberellin)能够刺激植物生长。现今赤霉素喷洒在葡萄上,可使果实长得更加饱满,并且不那么紧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生物化学教授理查德·阿马辛诺(Richard Amasino)教授说:“许多植物生理学研究都在寻找这种类型的信号,但是开花的信号还没有被发现,尽管许多植物在实验中都被磨碎。”
二十世纪70-80年代,植物科学家仍未找到开花的生物化学秘密,阿马辛诺说:“我刚开始搞科学研究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了揭晓这个谜团,揭开植物记忆的面纱,科学家需要了解分子遗传学,特别是表观遗传学,它是一种控制特定基因开关的机制。
近年来,科学家意识到基因本身无法决定一种生物体的命运,很多与DNA有关的表观遗传活动会造成一系列影响,例如:哪些遗传密码被表达,或者转化为行动。成花素(Florigen)是一种微型蛋白质,其体积太小,以至于梅尔彻斯这个年代的科学技术无法识别它们。即使他们发现了成花素,也很难揭晓关于什么因素使两年期植物开花的秘密。另一方面,阿马辛诺这一代科学家最终找到了植物记忆活动性的正常水平——表观遗传层面,并观察这一活动的过程发展。
▲左图是非春化植物,右图是春化植物
例如:控制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春化和开花的机制,这种植物经常作为实验研究对象,就像以鲁布·戈德堡机械方式进行蛋白质和基因表达,拟南芥拥有一组控制蛋白质形成的基因,该蛋白质可以促使该植物开花。在春化之后,拟南芥细胞中充满第二种蛋白质——FLC,它能够抑制促使植物开花的关键基因表达。但是当植物暴露在寒冷的环境中,它的细胞将缓慢制造FLC蛋白质,直至停止下来,同时,蛋白质的平衡发生改变。拟南芥细胞开始制造越来越多的促进开花的蛋白质,直至植物准备盛开绽放。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方法是将表观遗传行为作为一个开关。降温对于细胞可作为一种信号,转换其基因表达,从“不开花”至“开花,开花,开花”。即使当降温的信号消失,这种开关机制仍会保持启动状态。因此,当白天时间变长,植物会知道此时应该是开花的最佳时机。阿马辛诺解释称,即使在春季和夏季,寒冷也只会保留为一种记忆。
遗忘可能是比植物记忆更强大的生存工具
植物能够暗自记忆,在它们接收到每一个重要刺激时能开启或者关闭表观遗传行为吗?这好像不太可能,2016年,一支澳大利亚植物科学家研究小组在《科学进展》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他们认为,对于植物而言,遗忘(或者说根本不形成记忆)可能是一种比记忆更强大的生存工具,而且记忆(尤其是表观遗传记忆),很可能是一个相对罕见的事件。
该研究报告第一作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学家彼特·克里斯普(Peter Crisp)的工作是对植物施加压力,他和同事可能停止对植物浇水,使其处于缺水状态,之后再浇水,观察它们如何恢复。他们已证实某些植物对于干旱、低光照和食草动物的压力能够形成表观遗传记忆,并且“世代相传”。因此,克里斯普和同事对好几代的植物进行了观察,发现这些植物能否记得它们曾经历过的干旱经历,并且是否变得更加耐干旱,克里斯普说:“我们并未观察到这种现象。”
克里斯普指出,植物从压力状况下恢复的速度非常快。在今年夏季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克里斯普和同事发现受到光线胁迫的条件下,植物能够很快恢复,只要获得正常护理,疏忽照料、枯萎的棕色盆栽植物也能焕发生机。目前,科学家现已报道了许多植物形成记忆的实例,在科学家发布的实验结果中,植物原本可以形成记忆,但是选择遗忘的例子却很少。该研究领域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辨别植物是否已经形成某段记忆。
当克里斯普和同事们设计实验室研究时,他们必须控制很多混淆因素,从而确定是否他们所观察到的任何植物记忆是实验室压力所形成的结果。该研究报告合著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家史蒂芬·艾臣(Steven Eichten)说:“不是说植物经历过什么就会说,‘噢,我记得这个!’它发生于某一化学性状,一种分子层次的变化。”
识别这种变化并将其应于实验压力是很难的,甚至当科学家知道一种记忆来自一种植物,但他们未必能够识别另一种植物的记忆。例如:这种记忆机制涉及到阿马辛诺研究的FLC蛋白质,该机制仅适用于拟南芥。甜菜和小麦具有其独特的春化现象分子机制,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却独立进化,该研究领域识别一段真实的记忆是非常困难的。
在他们的实验中,克里斯普和艾臣并未观测到许多植物能够形成记忆,他们置疑:植物记忆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否是因为对于植物而言遗忘是更好的选择?
艾臣说:“形成一段记忆并对你以往环境接受的信号进行分子层面的跟踪,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由于我们并未经常观测到植物的记忆,或许植物并不希望一直记忆事物,很可能它们将能量用于其它方面。”即使当记忆形成,它们也可能消退。另一支研究小组已证实,一种植物在盐分胁迫下,可能会形成静观性遗传记忆,并将其遗传给后代。但是如果这种压力消退,记忆将随之消失。一种植物记忆太多,可能会以牺牲健康成长为代价,它们需要时刻提防干旱、洪水、盐和昆虫等威胁。或许植物会忘记那些消极的体验,而是将更多能量用于应对最糟糕的情况。
植物记忆的存在意义
我们试图通过自己的世界经验来理解植物的记忆和认知,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用“记忆”这个可以唤起人类的共鸣,来描述植物行为,这就是一个典型实例。艾臣说:“我们使用了‘植物记忆’,但是你能找到其它方法来描述它。但是‘半遗传性染色质因素(semi-heritable chromatin factors)’并不像植物记忆那样清晰易辨认。”
艾臣指出,有时我必须试着向我的妈妈解释自己的工作,我会说:或许这就像是一段记忆,即使你联想到人类记忆,这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对吗?你可能会想到神经连接,但在日常对话中,你一想到记忆,就能对记忆产生大概的认知。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关心记忆的本质,也不关心与其相关的特定神经元。
这与莫妮卡·加利亚诺看问题的角度十分相似,作为一名生态学家,其研究植物记忆的方法不同于分子遗传学家,她对记忆形成的兴趣比她在学习过程中要少。她说:“当然,植物是有记忆力的,我知道植物的行为是发生在意料之中的,在满足条件A的情形下,一棵植物应当可以完成事件X,既然它能够完成事件X,就证实它必须记清此前发生的事情,否则是无法完成事件X。”
叶片紧闭的含羞草并非莫妮卡研究的唯一植物,在另一项实验中,她用一个Y形迷宫培育豌豆,并测试它们能否懂得协调不同线索:风力和光线,植物朝向光线方向生长,在实验中莫妮卡添加了另一个附加线索,风扇产生的气流。对于实验中的一些豌豆,光和气流来自Y形迷宫的相同一侧,而对于其它豌豆,光和气流来自相反的方向。
莫妮卡说:“豌豆不仅要学习有用的东西,还要学习分辨哪些事情毫无意义,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系。在含羞草实验中,只需搞清楚一件事情,跌落意味着什么?而在豌豆实验中,则必须考虑两个重要因素——风扇和灯光。”
对这些豌豆训练之后,莫妮卡挡住了光线,当她将风扇转换至Y形迷宫另一侧后再次打开,希望观察是否豌豆已经学会协调气流和光线,或者在没有光线照射的情况下,豌豆是否足够健康,并对微风刺激做出反应,或者将风扇转至另一个方向,也没有光照信号。结果显示,受过训练协调气流和光照的豌豆朝向风扇方向生长;受过两种刺激训练的豌豆则背朝风扇方向生长。
她说:“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植物当然都有记忆了,不然训练怎么会有效呢?记忆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负责学习的是谁?学习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将气流和光线联系在一起?”
这表明莫妮卡使用了“谁”这个词,许多人不太可能用这个词指植物。尽管植物有生命,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它们不是动态、会呼吸、会生长的生物,我们将其看作是对简单刺激做出反应的机械性行为。但在某种程度上,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是这样的,它们是化学物质和电信号的结合体,能与所处环境进行交互。记忆是一系列外部刺激留下的生物化学标记,例如:2016年夏季沙滩度假时感受到的热浪。几个月寒冷冬季产生的一种植物表观遗传记忆从本质上与夏季热浪记忆是差不多的。
- 折叠屏手机成为各大厂商发力的对象 2022年出货量有望达1750万台
- 酷比魔方新品iWorkGT发布 配11英寸全贴合屏幕 功能接口齐全
- Xbox One主机确认停产 官方表示将在2022年重启PS4的生产线
- 外挂开发商通知将停止对《战地2042》外挂更新 不值得继续维护
- 三星全新显示技术QD-OLED将是香饽饽 带来的画质提升让人充满期待
- 曝天玑9000旗舰手机春节后登场 包含一些真正的顶配旗舰
- 微信红包变样了! “摇动”手机即可领取SS22异形红包封面
- 2021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榜 阿里巴巴位列榜单首位
- 锂电池新型电解质面世 可以有效抑制锂枝晶的出现
- NVIDIA获评美国最佳工作场所 NVIDIA获得榜单第一的宝座
- 东北女子网购金鱼收到冻成冰坨 网友热议网购生物不合常理吧?
- 小鹏汽车转让嘉兴智鹏全部股权 新增股东嘉兴鹏行将100%持股
- 《长津湖之水门桥》定档大年初一 今年春节档的动画电影多达5部
- R星母公司T2财报暗示 计划在2024年3月前发布《GTA6》
- 手工耿发明第二代卫生纸加热器 网友调侃直接发明加热马桶多好
- 通用汽车高管:公司待上线CarBravo网站将便于用户购买二手车
- 挑战锂离子电池的锂金属电池来了 多家龙头公司的同时参股
- 女子网购iPhone遭快递员强拆验货 网友表示快递员估计以前吃过亏
- 北京冬奥会火炬将在三个赛区传递 “飞扬”的材料采用了“碳纤维”
- 保时捷2021年销量创下全新纪录 Taycan等电动车款式增势喜人
- IDC副总裁: 今年PC市场或迎来进一步发展 但同时存在诸多挑战
- Intel Arc显卡冒出来20个版本 这些设备ID目前都是禁用状态
- 苹果认证配件商推出145元抛光布平替款 支持多次水洗
- 脑瘫女孩求输入法“破解” 搜狗输入法团队接手这个输入法
- 时隔5年再次拥抱AMD显卡 发布了自己的RX 6600 XT
- 母亲被指“老赖” 女UP主致歉 决定退出B站评选的百大UP主
- Intel未发布下代至强被开盖 每颗计算芯片上有16个核心
- 全球首个家用万兆Modem测试成功 上传速度超过了4Gbps
- 舅舅给外甥包50亿红包只值5毛钱 网友调侃这版好几年前已经作废了
- 曝英伟达将加强首批RTX3050货源铺货 到仓时间预计为春节后
- AMD的锐龙7 5800X3D处理器曝产能紧张 增加了额外64MB缓存
- 索尼FX6电影摄影机即将发布新固件 虚化调整模式等新功能将至
- 撼讯RX6500XTmini-ITX显卡或下周上市 GPU实测频率尚待公布
- 抖音又有大动作!封禁52万个涉嫌诈骗账号
- PowerToys工具集发布v0.53.3正式版 软件运行速度将获提升
- 微软推出Win11最新Dev预览版 将重置天气小部件优化体验
- 微软Xbox负责人:比起XGP 游戏玩家还是更注重传统销售方式
- MIUI13稳定版已推送至小米10S手机 基础体验将得到更多优化
- 戴尔高级副总裁谈XPS13Plus新品:全为创作者开发升级众多
- MIXFOLD2折叠机曝光 外屏更换为玻璃材质 ID设计发生变化
- 索尼原计划停产的PS4确认继续生产:旨在缓解PS5无货状况
- Canalys最新数据表明:个人电脑全年出货量已同比上涨15%
- 英飞凌官宣最新一代CAPSENSE技术 并可提供多个先进解决方案
- Redmi官方发布蜘蛛侠联动海报 以其迅捷身手宣传120W秒充
- OPPO首席产品官刘作虎点评新机一加10Pro:表现全方位的稳
- 百度起诉我爱网获赔200万 帮助用户制造虚假点击数据
- 国产虚幻4大作上架国行PS商店 将收录目前所有游戏更新的扩展内容
- 雷军回忆小米12“黄金手感”诞生过程 澄清很多消费者的一个误区
- 搜狐CEO张朝阳登上长白山开启超长直播:三天三夜出镜不间断
- 统信操作系统V20龙芯版正式发布 拥有人性化的桌面环境
- 传iPhone14Pro将升级4800万像素广角镜头 影像力进一步提升
- 罗技发布LitraGlow照明设备 可为流媒体视频录制提供更好的打光
- 索泰RTX 3080 12G6X PGF OC显卡图赏 支持ARGB灯效分区控制
- 四盘位NAS极空间新Z4图赏 采用Intel J4125处理器
- Microchip发布全新编程开发工具MPLAB ICE4 速度已达到极致
- Redmi Note 11S宣布 采用类似Redmi Note 11的矩阵相机设计
- 高端新能源SUV销量榜 宝马iX3是BBA电动车中销量最高车型
- iPhone14手机定价曝光 全部型号一致比苹果13系列高出一百美元
- 一加蓝帅称OPPO/一加社区可能联合举办活动 但暂未有合并计划
- vivoNEX5核心配置遭曝光 或惊喜配置7英寸大屏幕以及长效续航
- Redmi《蜘蛛侠3》联动引热议 网友开喷发了几张海报就算联名了
- NVIDIA为7年前Shield TV升级安卓11系统 带来一些功能升级
- OPPO进入21年度美国专利授权榜Top50 总719项授权同增三成
- 徐起盛赞真我GT2Pro超大内存版:为年轻用户带来更大存储空间
- Firefox96正式版来了 可兼容Win/Linux/macOS 运行速度起飞
- 老赖拖欠20多万不还 B站CEO陈睿“力捧”其女儿至百大UP主
- 湖南小伙隐居深山4年造出一个桃花谷 网友评论实实在在的扎根农村
- OPPO K9x机型也推出限时立减 可选两款配色 大容量电池续航长
- 宁德时代申请无负极金属电池专利 能量密度为160Wh/kg
- 2GB内存的树莓派4就能跑Ubuntu 22.04 背后优化的秘密是Zswap
- 大屏版Android 12L放出Beta2 系统特性和API已经定型
- 传长城和路虎成立合资公司 长城汽车正面否认该传闻
- RTX 3050供货将大大增加 预计渠道方面大量开卖要等到春节后
- 报道称新款27英寸iMacPro将在三月推出 并采用M1Max处理器
- 博物馆将名画夜巡数字化并发布超高清照片 细节纹路分毫毕现
- 爆料称iPhone 14将采用双开孔设计 是感叹号形状的开孔
- 荣耀总裁科普Magic V折叠屏 向设计能力和制造工艺发起挑战
- realmeBook增强版笔记本推出年货好价 极致轻薄机身更易携带
- 三星Galaxy Tab S8高端平板现身韩国认证网站 屏幕均采用四等边框
- 一加李杰解读新旗舰外观:全新材质打破常规 细节用心质感更出众
- 红魔7跑分出炉 将搭载主动散热级骁龙8 Gen1
- 魅蓝回归第二款新机入网 3C认证信息显示该机将支持10W充电
- 小米10S推送MIUI 13稳定版 搭载号称业内最好的双立体声扬声器
- 三星手机与京东战略合作 全方位提升三星在国内手机市场的销量
- 集邦咨询:预测今年智能机相机模组出货量将持续增长至49.2亿颗
- 飞傲正式推出FHE圈铁耳机 新品支持换线使用 高频延展表现佳
- 消息称Redmi K50系列全员打孔屏 将会推出冲击高端价位的机型
- 京东上架荣耀Magic V茅台套装版 将于1月18号首销
- Intel锐炫显卡完成重要优化 一经发布即可用上强劲Linux驱动
- 曝Redmi K50电竞版保留侧面指纹 将指纹模块嵌入功能键中
- 曝iPhone 14 Pro采用双挖孔屏幕 圆孔存放Face ID的点阵模块
- 曝谷歌Pixel Fold神似OPPO Find N 谷歌Pixel Fold代号为“Pipit”
- 丰田全新坦途Capstone皮卡来袭 外观用上整车镀铬装饰尽显豪华
- 一加10 Pro正式开售 采用三星6.7英寸AMOLED顶级屏幕
- 曝vivo NEX新品用7英寸超大屏 后置主摄为5000万像素
- Intel奔腾G7400处理器上架销售 多款新酷睿i5处理器也已开卖
- 中国电信推出天翼空中上网产品 支持在线音视频等办公及娱乐服务
- 英特尔赛扬G6900入门级处理器水准分析:单核胜过i9-10900K
- 小姐姐实测小米12 Pro充电 速度位列第一梯队
- realme GT2 Pro首个系统更新 新增视频模式Al视频增强功能
新闻排行
- 酷派手机:将追究快手主播“驴嫂平荣”直播间售卖山寨机的责任
- 荣耀平板V7 Pro今日开售 采用高导热铝合金中框
- Redmi 10在马来西亚举行发布 采用居中挖孔屏方案
- iQOO 8 Pro作为iQOO最强大的旗舰 首发多项核心技术
- 小米平板5 Pro 6GB+128GB版本现货发售 支持67W闪充
- 飞行员iPhone X从3千米高空跌落 因戴配套保护壳幸运保持完好
- 一加Nord 2 5G手机将于近日在海外发布 搭载天玑1200-AI处理器
-
 小米手机屏下摄像头专利上月获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授权
小米手机屏下摄像头专利上月获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授权 -
 OPPO将为旗舰机带来最大7GB内存扩展 为低内存手机带来更好的体验
OPPO将为旗舰机带来最大7GB内存扩展 为低内存手机带来更好的体验 -
 荣耀选择单电芯双回路技术 提高快充速度是目前解决用户“电量焦虑”问题的方法之一
荣耀选择单电芯双回路技术 提高快充速度是目前解决用户“电量焦虑”问题的方法之一
精彩推荐
超前放送
- 京东家电年货节盛大开启 多家线...
- 红米K50电竞版工程机曝光 爆料...
- 红魔7新机入网 后置摄像模组为...
- 最新版高德地图推出超好用功能 ...
- vivo最新上架Y10与t1新机 定价1...
- 育碧新版工人物语预告视频来了 ...
- 华硕破晓Pro15笔记本:搭载全新...
- 摩托罗拉edgeX30喜获2021最具影...
- 小米音频输出模式调整相关专利获...
- INNOCN海外发布全新4K液晶显示器...
- AppleProCam8K视频相机新图曝光...
- IP衍生手游《阿凡达:清算》首曝...
- 索尼将停售PlayStationNow储值卡...
- Noble限量耳机VIKING正式发布 ...
- 小米CEO雷军:又有一款产品全量...
- 散热器厂商Noctua更新产品路线图...
- 传TOP5大厂旗舰新品将用上12/13...
- 爆料称新款锐龙4000系列桌面处理...
- 不带身份证也能坐火车了!12306...
- OPPO新品现身Geekbench 测试者I...
- 福特汽车官宣:去年已完成覆盖范...
- 方形版小米智能手环专利获得授权...
- 七彩虹高端硬件显卡新品上架京东...
- 比亚迪全新测试车谍照曝光 外壳...
- 2022年油价第一涨!加满一箱92号...
- 小红书申请老红书商标获批 网友...
- 4月北京骑共享单车需实名认证 ...
- 福特超级跑车现身拍卖网 搭载一...
- 酷派COOL 20 Pro敦煌鎏金版开...
- 小米12系列即将亮相海外 Pro版...
- Redmi K50电竞版工程机参数曝光...
- 小米12 Pro新年礼盒版明天首销...
- Redmi Note 11S外形曝光 后置...
- 英特尔Arc锐炫显卡忽现20个新版...
- 黑鲨游戏手机新旗舰曝光 该机将...
- 调研机构:21年第四季度HDD出货...
- 萤宝虎年限定礼盒来了 拥有十八...
- 英特尔待发布处理器已被拆解开盖...
- 爆料称多款RedmiK50系列机型将采...
- 小米与多家高校共建工作室陆续启...
- 三星全新笔电设计专利获批:键盘...
- OPPO FindN手机再次开售 定价...
- 乂度最新解码耳放Link2Bal发布 ...
- SurfaceLaptopSE维修视频上线 ...
- 设计师详解小米12系列后置摄像模...
- 等老了改名吗?小红书成功注册老...
- OPPO Find N今日10点再次开售...
- 电竞手机红魔7入网 该机整体延...
- 红魔7入网照片公布 后壳采用大...
- K50 Pro系列曝光 Redmi K50搭...
- 曝天玑9000机型3月上市 安兔兔...
- 12306手机App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
- 全新丰田Noah/Voxy官图发布 新...
- 丰田GR YARiS GRMN发布 拥有...
- 大众集团发布销量报告 大众中国...
- 五菱E230专利图曝光 将提供更小...
- 宏光MINIEV 2021年销量42.6万台...
- 北京越野BJ40环塔冠军版交付 采...
- 日产全新跑车Z开售 采用标志性...
- Xbox产品营销高级总监:为专注于...
- 英特尔i7-12700盒装处理器来了 ...
- XboxSeriesX|S在英国达成百万台...
- 荣耀公布使用可穿戴设备排队叫号...
- 英伟达高管:公司显卡供应短缺状...
- 原神安卓版更新上线 对骁龙8/天...
- 乘联会现发布12月销量排名快报:...
- 雷蛇2022款灵刃14笔记本:标配R9...
- 索尼发布无线颈挂式扬声器新品 ...
- 昉星光VisionFive单板计算机已完...
- 宁德时代无负极金属电池专利曝光...
- 索尼电影公开神秘海域宣传海报 ...
- 体验玩法大更新 游戏宝可梦传说...
- 徕卡M11相机上架天猫并公开售价...
- 消息称小米正积极开发12款新机:...
- 英伟达SHIELD机顶盒更新9.0系统...
- 曝三星GalaxyTabS8系列有望即将...
- 传天玑8000新机将配置6.6英寸120...
- BlueTiger发布Solare太阳能耳机...
- 酷派COOL20Pro敦煌鎏金版正式发...
- 全球汽车销冠出炉 大众高端品牌...
- 轩辕剑柒上架索尼PS国行版商店 ...
- 雅迪亮相米兰国际摩托车展 采用...
- 奇瑞瑞虎8 PLUS鲲鹏e+预售价公...
- 90后艾玛沃特森晒新写真造型 全...
- SATA SSD硬盘爆出安全漏洞 美...
- 索尼发《神秘海域》中文预告 计...
- 路虎混动新车就出故障 4S店回复...
- 比亚迪中标智利锂矿开采 每份合...
- 蜂鸟Logo被“元宇宙项目”侵权使...
- NASA发布新一代太空望远镜主镜片...
- 映泰上架B660GTN ITX主板 将使...
- 《尼罗河上的惨案》新预告 故事...
- 近百只鸵鸟在广西街头狂奔 出现...
- 2022款ROG幻13晒出官方图赏 国...
- 年度最佳游戏终于登陆PC 该游戏...
- iPhone 14 Pro系列展望: 将...
- 《007:无暇赴死》1月15日登陆B...
- QQ音乐推出超级会员 专享免费线...
- 凤凰Phonenix-6静电圈铁耳机正式...
- 火狐官方回应新版浏览器无法访问...